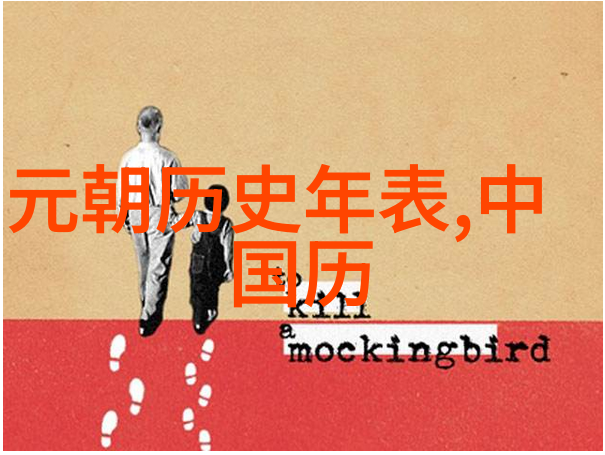在我走过的近半个世纪的科研生涯中,我,庄文颖,已经很少再去野外考察了。曾经,我踏着坚定的步伐,在全国26个省份的荒山野岭上征战;我的肩膀背负着数不尽的真菌标本;我的双眼辨认出了360多个新种。如今,随着岁月流逝,我步子沉重了些许,背微微有些弯曲,但眼睛依然闪烁着对真菌学无尽的热爱。我依旧留着端庄又好打理的齐耳短发,每天出现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C座4层实验室,与真菌标本、放大镜、显微镜和她的学生为伴。

荣誉纷至沓来,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美洲真菌学会外籍荣誉会士”,学者们还以我的名字命名了真菌新属“文颖盘菌属”和细菌新属“海庄文颖氏菌属”。最近,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科协等部门首次联合开展的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中,我被遴选为2021年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但我最看重的是那个最简单且亲切的地位——“菌物学家”。
30岁那年,当我踏上了真 fungi 学这条路时,一场新的旅程即将展开。在1968年的春日里,当响应国家号召我到农村插队时,那是一个充满未知与机遇的时候。那时候,只要有空余时间,我就会抱起书本,用心探索世界。1973年的秋天,当机会降临于我之时,她让我顺利考入山西农学院,并在毕业后选择留校任教。当时,有两个选择:昆虫学和植物病理学。“不喜欢昆虫”的我选择了植物病理学。在边教边学习期间,我发现,大约70% 的植物病害是由真 fungi 引起,这也让一个问题悄然浮现:为什么我们不能更深入地研究它们?

带着这个疑问,我决定继续前行。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师从当时国内著名的 fungus 学家余永年,“踏上了真正意义上的 fungus 学之路”。那一年,是我30岁,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时间飞逝,在一次次实验与思考中,我们一起成长。在余永年的指导下,我掌握了一门门有关 fungus 分类系统化方法,不仅成为课题组里的顶梁柱,更是在他面前的智慧灯塔。他期望我能够为我们国家 fungus 分类研究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的科学工作走向世界。这段时间,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是一次难得的人生旅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即使休息时间有限,也用心学习,因为那里有很多难得关于 fungus 的文献资料,以及国际同行们高效率的一面。

1988年回国后,那份渴望让国内学者了解国际期刊并非不可攀登的心情驱动了我们。我和十几位同行深入大巴山丛林进行野外考察。那次考察归来,我们团队成员在国际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一组(7篇)论文,让中国 fungus 学家的身影第一次亮相于世界舞台。
“我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但这么多年来,无论是艰苦卓绝的野外考察还是繁忙而专注的情报搜集与分析,都让我感受到了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而那些曾经的小小困惑,现在已成为过去,而那些曾经的小小希望,现在已成为了现实。

回忆起往昔,那些记忆如诗如画,如同梦境一般温柔而神秘。但这些记忆并不只是停留在过去,它们激励着今天,还将指引我们的未来。当有人问及我的事迹,或许会说:“她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但对于那些曾经跟随在她身后的学生或同事来说,他们知道,这是一句极其谦逊的话语。她所做出的贡献,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增加,更是在科学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她给予我们灵感,她给予我们力量,她也给予我们勇气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标签: 东汉之前是什么朝代顺序 、 中国古代的朝代顺序表 、 中国历史朝代更替表 、 历史顺序表完整版 、 明朝那些事儿txt全集下载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