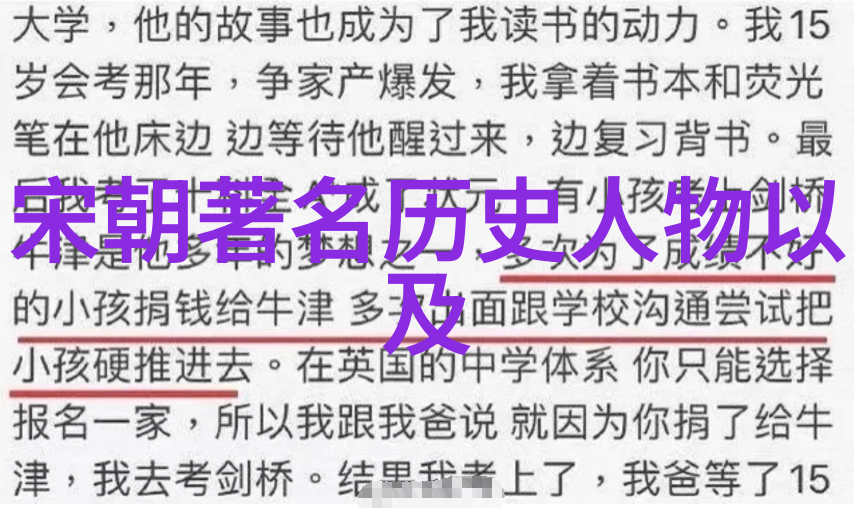我,马玙,在58年前与一位病人建立了联系,这段经历至今仍让我感激不尽。尽管我的年龄已经接近九十岁,但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里,我一直致力于结核病的防治工作,无论是诊疗、科研还是教学。我一直坚守在这个领域,一直在这场与结核病的斗争中奋战。

我对此感到坦率,作为一名临床医生,被评为“最美科技工作者”这样的荣誉,我有些不好意思。这不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价值,而是我认为作为临床医生,最重要的是关心和治疗患者。我并非纯粹的科研人员,我所做的一切实验室研究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临床研究,为我们的诊断提供支持,比如血清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技术。
1955年,当我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工作。那时,研究所位于通州,是一个偏远的地方。在那个时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结核病流行,这是一种非常难以治疗的疾病。面对这种情况,我并未退缩,而是选择了这一条道路,将其成为我的毕生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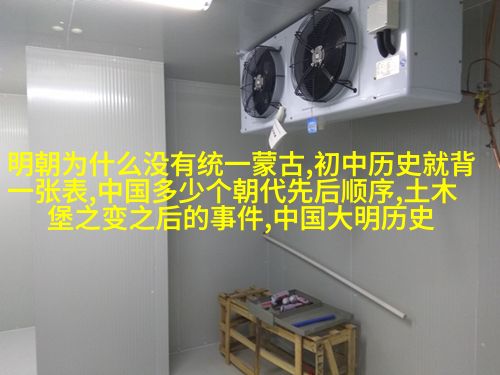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搞研究”更多的是迫不得已。当回忆起自己的科研成就时,我深感自豪。在那个时代,我们只有很少的手段来治疗结核病。“灵丹妙药”几乎无处寻得。耐药性是一个关键问题,有些患者会耐受一种药物,有些甚至因不当治疗而出现全身耐药。在诊断过程中,我们需要快速了解患者是否有抗药性,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因此,我和同事们开发了一种使用基因分子生物学检测各种药物相关耐药基因的技术,这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诊断效率。
改革开放后的年代,对于科学家来说是一片新的天地。我成了博士生导师,并指导许多基础扎实、充满活力的研究生,他们带来了新的能量。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在我的引导下,他们承担了大量任务,成为了探索新知识的大将。而现在,看看他们取得的成就,都超过了我自己。这让人既欣慰又高兴。

回想起三四十年的往事,一次国际交流中的经历尤为难忘。一位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教授曾到访我们的实验室,他看到我们对于抗结核菌株产生抗药性的研究结果,就拿出照相机拍照。当他被问及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回答说,他想让那些总抱怨条件差的小学生看看中国科学家如何在小小实验室中完成前沿级别的研究工作。
虽然过了一半世纪左右,但人类与结核杆菌之间持续不断的地球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这场战争中的敌手不断变异,其它类型也正在发展出抗藥性,与新型藥物展开长期较量。但正如我所言,在这场漫长战斗中,不论何种形式,只要遵循早期发现、联合用药、高剂量、全程控制以及规律服用,即“早、合、大全规”,这些基本原则不会改变。此外,还需要所有参与者——包括医生、中介角色乃至患者——共同努力,只有如此才能确保这一战斗能有效进行下去。而我,就是在这一战壕上站岗六十余载。(孙明源)

标签: 中国大明历史 、 明朝为什么没有统一蒙古 、 土木堡之变之后的事件 、 初中历史就背一张表 、 中国多少个朝代先后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