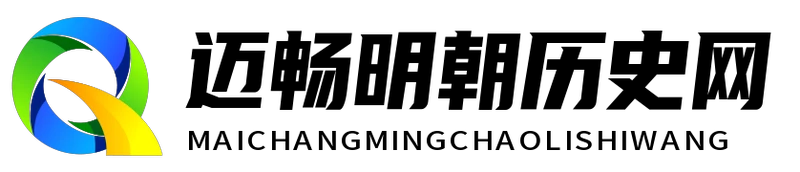在我走过的科研道路上,已经有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曾经,我踏足了全国26个省份的荒山野岭;我的肩膀背负着数不尽的真菌标本;我的双眼辨识出了360多种新物种。随着岁月流转,我步伐沉稳,背影微弯,眼睛偶尔也会不受控制地涟涟泪下。我依旧留着端庄且易于打理的齐耳短发,每天都出现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C座4层实验室,与真菌标本、放大镜、显微镜和学生们为伴。

我拥有许多荣誉,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美洲真菌学会外籍荣誉会士”;学者们还以我的名字命名了真菌新属“文颖盘菌属”和细菌新属“海庄文颖氏菌属”。最近,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科协等部门首次联合开展的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中,我被选为2021年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但我所珍视的是那个最简单而温馨的称呼——“菌物学家”。
30岁时,我踏上了真 fungi 学这条路。在1968年的春天,当20岁的小姑娘庄文颖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农村插队时,她带去了对书籍深厚的情感。那时候,只要空余时间,她总是抱起书本。1973年,那束光明照进她生命中的机会来了。她顺利考入山西农学院,并在毕业后选择留校任教。当时,面前有两个选择——昆虫学与植物病理学。“不喜欢昆虫”的她选择了植物病理学。在边教边学的过程中,她发现,大约70%的植物病害由真 fungi 引起,这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值得研究。

带着这些问题,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在师从著名专家余永年的指导下,“踏上了真 fungi 学这条路”。那一年,是我30岁。我掌握了分类研究方法,成为课题组里的顶梁柱。师生间默契日益增强,我们知道对方想做什么,而余永年也深信我能将他的期望实现。
1983年,在缺人手的情况下,余永年决定送我赴美进修并攻读博士学位。他期望未来能为国培养一批优秀科学人才。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到了许多难得文献资料,也见证了国际同行高效率工作,那段时间里,我努力压缩休息时间学习工作。在返回国内后的1993年,一次丛林考察成为了关键转折点。这次考察归来,我们团队成员连续发表7篇论文,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

回忆过去,对于那些艰苦卓绝却充满诗意的地方,比如广西的大龙山或是新疆戈壁滩,或许有些人觉得它们只是地方,但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承载着无限记忆和探索精神。“他留下的,有用的我肯定要用”,这是对老师遗嘱的一份承诺,同时也是对热情与执着生活态度的一份致敬。
尽管身体已然七旬,但我的热情与执念依旧燃烧如火。我坚持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编辑工作,为学生修改论文,用心陪伴他们每一步成长。而对于未知领域,即使身处晚暮之际,也仍愿继续学习,不断拓宽人们对真 fungi 学认识之界。(倪思洁)

标签: 万历 是明君还是昏君 、 康熙最漂亮的老婆 、 乾隆为什么讨厌雍正 、 元朝简介及历史概述 、 孙若微和朱瞻基